
1.
他叫雪橇,是我的朋友。
2.
我总会和别人谈及雪橇。
在我的描述中,雪橇是一个有着淡淡而又清晰的鬓角的男孩子;他略胖,但并不臃肿,体型是刚好能够撑起各种衣服的形状;他健壮,但没有棱角分明的肌肉,因而他软软的,柔软如填充毛绒玩具。
我的描述具象而又模糊,因描述而构建起的人物形象会在顷刻间褪色斑驳。我身边的朋友们在听完这段描述后常常称赞“他真的好完美哦”。我坦然接受他们的赞美,并对他们眼睛里的疑惑置之不理。
出于某种原因,雪橇总是一个轻盈而又洁白的形象。他迷人,但不具有迷惑性;他让人靠近,又给人以疏远和不和谐的距离感。他总能在阴郁的天气里像一束阳光般照亮我的生活,但却也只是像一束光一样的缥缈和不可捉摸。
雪橇是一个柔软的男孩子。他像是一朵云,轻盈而又湿润。他说话有软软的口音,笑起来有着软软的皱纹,甚至连他发给我的短信,字体也磨去了宋体字生硬的棱角,变得柔和而又亲切。他的柔软普适与各种介质: 通话、文字、FaceTime 或是物理上的接触。这种柔软仿佛天生自带通感,可视信息会同时带给你可听可触的感觉,并同时激发平和惬意的反馈。
只是我主观角度的揣摩和发散,在事实上可能会有一些晦涩的区别。
我会给他发短信,也会很快收到相同内容的回信。出于此我便大胆地猜想雪橇一定是一个冷幽默而又一丝不苟的人,帮助我做出判断的还有每次两倍于我发信时间的回信时间。我认为他是一个英国人,严格的右翼,更甚者,他或许是一台机械,按部就班地在晶体管连接下处理类似 0100101 的讯息。
正如他如一片云一样的轻盈,他也如一朵云一样的易于塑性。他或高或矮,或黑或白。他像是一片命题作文,在大纲框限下被反复艺术加工,变化形象,并产生白云苍狗类似的幻觉。但又不同于幻觉,每一个雪橇都是真实存在的(或存在过的)。不同的雪橇串联成一条时间线,并不断往返于过去、当前与未来之间。他有点像一个 psd 文件,由不同的可替换的图层组合而成,凭借(全凭)用户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进行艺术加工与再塑,并饰以癔症与偏执的滤镜。
这是雪橇,我是他的朋友。
3.
我在社交软件上看到了雪橇最近的照片。他还是那个软软的男孩子。
我在雪橇这个账号下面点了关注,系统提示我关注成功。随着一个小红点出现在我的资料页上,我的关注数从 246 上升至 247。
我对这一收获心满意足。雪橇像是又被填充进一团化纤的毛绒玩具一样显得更加柔软可塑。他的形象变得更加鲜明饱满,更靠近一个无需技术性观察便可感知及评析的形象。
雪橇便是在不断的修补和变化中完善的。我曾经试着将雪橇固定一段时间,但他很快便变得暗淡与荒芜,生满杂草。最终我不得不重新拾起洗衣液、润滑油与锄头重新劳作,才把他变回那个轻盈的男孩子。
我试图将这一点归咎为他自己没有搭配穿着的审美,只能依靠我来为他挑选日常配饰,因而没有我他便只好丛生些杂草枝蔓来掩盖窘相。
我的演绎符合逻辑,但这一切推导代入现实便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现实中的雪橇穿着个性又鲜明,总是走在社会审美认知的前列。他先锋而又保守,让人眼目一新的同时又兼顾一些“文化捍卫者”的滞后思维。
逻辑猜想虽与实际相悖,我还是坚持对实验现象选择性失明,固守这并非空穴来风的理论。
4.
另外的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被逐渐揭开。我与雪橇交往的方式从发讯息发电邮上升至了拨打电话或有时在语音信箱中留言。
我们通话时间不能算长,也没有周期规律。因此带来的一个好处是我每个月的话费账单除多出几元的语音信箱功能费之外并没有任何变化。我很惬意与这种低成本(无成本)的通讯关系,并也乐意与想寂静的手机听筒倾诉我乏善可陈的生活。我也习惯于听筒内传来的沉默或类似回声一样的错觉,并在通话结束后不通过触摸屏幕而是直接按下电源按钮来结束通话。但我每次按下电源按钮往往会点亮锁定的荧幕。透过长时间通话而沾上的油腻,荧幕恪尽职守地显示着日期时间和被设为壁纸的雪橇照片,这事和我通话的雪橇,这是于当下日期和时间的雪橇。我会盯着屏幕下方闪动的“滑动来解锁”字样,有时还有左上角“无服务”的提示。
我不会滑动去解锁,也不会在意是否无服务。
紧接着,我会再次按下电源键并尽由手机忠诚地在“咯嚓”一声中熄灭荧幕。
我还能从屏幕上观察到与雪橇通话的痕迹,然而也仅仅是痕迹,连同冰冷手机一同被装进兜里。
5.
我对于雪橇的描述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设定是,我与雪橇正在进行一段异地恋。
这是少数不随雪橇变化而变化的设定之一,我与每个雪橇在每个时间点都保持着这种关系。雪橇在上海,就读于某所大学,这一点也是不随雪橇变化而变化的。但话虽如此,得益于现代发达的通讯技术和运输工具,我还是可以让雪橇依据需要(甚至仅仅是无聊之举)出现在北京、武汉、青岛等各个城市。同时借助开放的社交网路,我也前所未有地容易去找到雪橇于不同城市的影像,并利用软件稍加修改,就可直接使用来佐证雪橇之于此地的真实性,而无需考虑版权或是其他技术上的问题。
我与雪橇一直保持着柏拉图式的恋爱关系。这是基于安全性的深思熟虑。抛开肉体上的俗欲,我便得以创作最引人入胜的雪橇而避免遭受“文化捍卫者”的严厉谴责。
我乐意维持这一兼顾有加的雪橇并不懈地构建与发展他。我通过新的状况了来不断填补之前的漏洞,并不留情地间断不自洽的红线,来保持情节的逻辑性。我也会每天抽出几分钟来对雪橇(和这段恋情)进行维护。
维护自然是通过无成本而又可轻易彰告世人的通话来完成。我能够精巧地通过我单方的语言来向听众演绎一个完整的情节,若辅之以结束通话后的喜怒哀乐更是使这一情节更加饱满而充满感染力。
我得以轻松地从各个角度来塑造每一个细节,便捷的社交工具功不可没。我通过脸书或微博对当下的情节加以雕琢,并通过创作聊天记录来将情节引入生活令其与观众们互动。这一方面可以更加有力地证明这些戏剧性的雪橇并非杜撰,另一方面也可以打破第四面墙,带来更加真实的体验。
我和雪橇的感情坚若磐石。尽管我们之间有(不得不有)规律性的吵架,但是事态会在可控的范围内发展,并以一个感人肺腑的结尾来开启下一步的生活。这种可掌控的关系自然会为人所称赞,同时也有许多感情受到一时挫折的人忿忿不平地窥视我的生活来宣泄无力感。我并不享受于此(或说这只是整个愉悦感的一小部分),我享受的是有由雪橇所打开和引领的一种全新的生活。
在那个生活里有着恰合我意的人和恰合我意的事。我可以想那个生活无顾忌地去陈述我当下这个乏善可陈的生活,或从那个生活中撷取一角投入当下的生活,并由此产生蝴蝶效应,牵连出当下生活中一些有趣的事情,并再次以之为素材向那个生活去陈述。
我建设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结构,透过这个结构我可以在当下与不同的雪橇所构成的世界中尽情往返。
这是整个愉悦感,将其带给我的人是雪橇,我的朋友。
6.
除去雪橇,我每天还会抽出时间写一部小说。
我更希望它变成一本日记。我诚诚恳恳地把我与雪橇之间的故事记录下来,但它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本小说。
我确实十分坦诚地把它当作纪实文学来写。我在其中详尽地记叙了我是怎样一步步地构建起如今这个雪橇,又是怎样一砖一瓦地拆毁他,并在原处再次修建另一个新的雪橇。坦诚至极,让我每次都仿佛看到赤裸的自己。
有一次我读到一本书。那本书上写,总是向日记宣泄感情的孩子都是社交无力的孤独症患者。我把那本书撕得粉碎。
我有朋友,好多朋友,他们也都是雪橇的朋友。我和雪橇拥有相同的朋友圈,并且也享受与这稳固的交集。
我喜欢在身边的人面前讲电话,大声的将自己的生活展示给别人。这让我有一种安全感,同时也给了我可以云淡风轻地面对社交关系的自信。
有了雪橇,我就不必再担心身边的人是否在疏远我;有了雪橇,我就不必再担心喜欢的人是否喜欢上了别人。
我有了雪橇,因而我不需要再去交朋友;我不需要再去交朋友,因而我不需要面对困难的社会交往;我不需要面对困难的社会交往,因而我不需要为自己的社交关系而苦恼;我不需要为自己的社交关系而苦恼,因而我不会受到伤害。
我潜居在我为自己构建的温室里,并感谢雪橇搭起了这个避难所。
7.
我想我正处于社交生活的巅峰时刻。我从未如此轻松地面对人际关系与友情或是爱情。
我可以冷眼旁观身边发生的一切来来往往的人所拥有的生活,或是客观的观察周围分分合合的各式关系。我也会擅自地对这些生活以自己的标准做出评价,展现出自己“情场高手”的身份。而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向我咨询社交上的建议,我也总会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回复他们,这样我便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
多好啊,我所拥有的这一切。而这一切都得益于雪橇,我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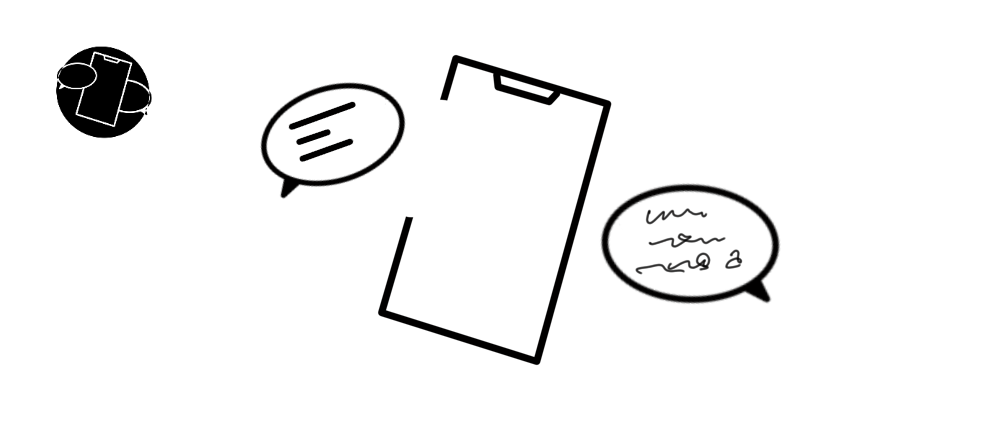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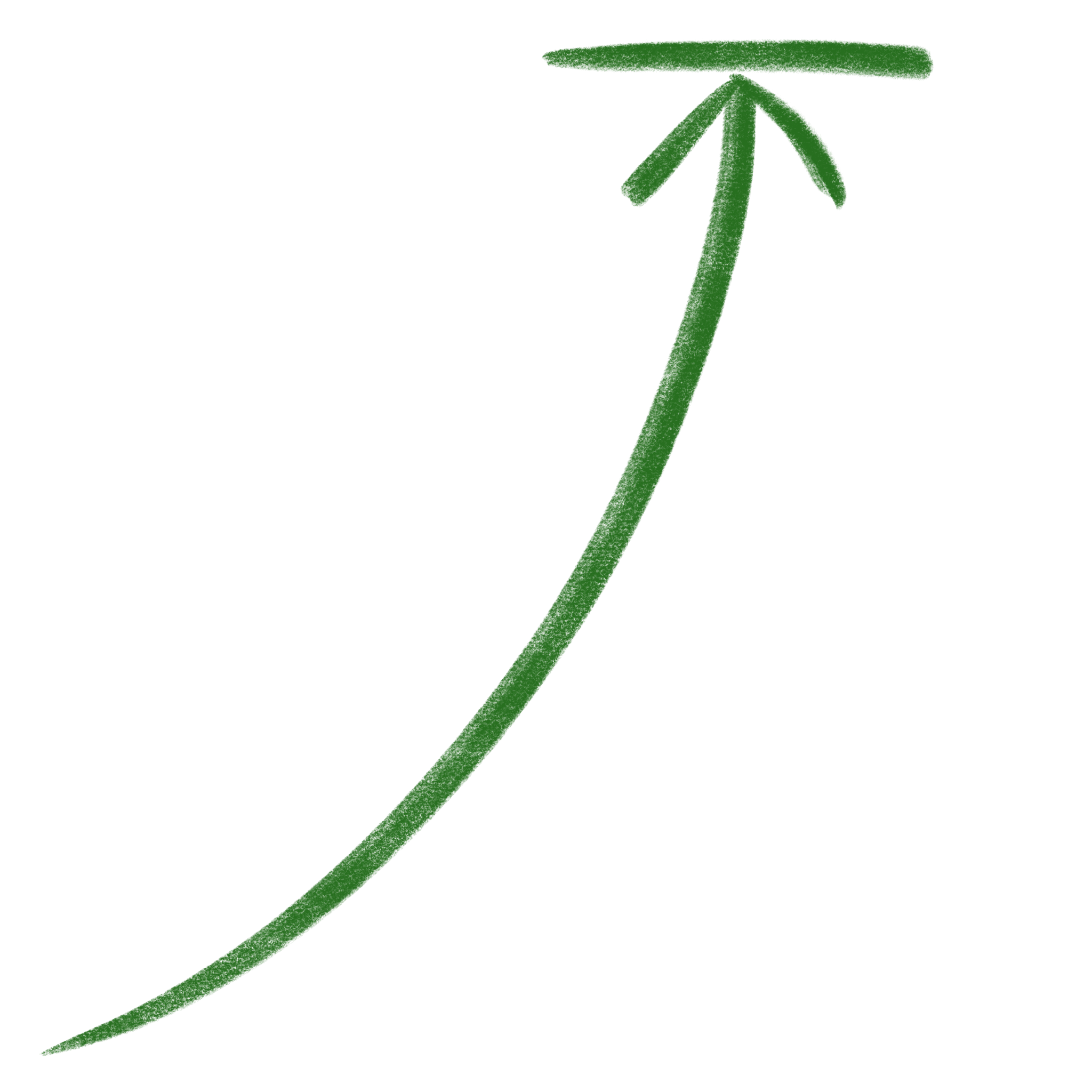
Leave a Reply to how to buy rifaximin buy in london Cancel reply